【党史人物】熊世忠:坚贞不屈的女战士李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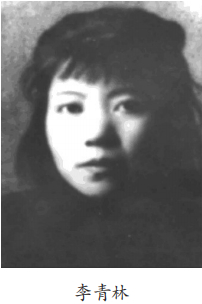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泸县人。李青林出生于泸县北城镇(今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一个商人家庭,在兄弟姊妹7人中排行第六,被称为“六妹”。幼时家境优裕,聘有家庭教师,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29年,李青林考入泸州中学读书。不久,因其叔叔欠下债务,债主强迫弟债兄还,并勾结驻泸县军阀向李青林的父亲逼债。父亲被捕入狱,遭到毒打,忧愤交加,病死狱中。随后,母亲董氏也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在兄姐微薄工资的资助下,过着艰苦的生活。家庭骤然而至的悲惨遭遇,使15岁的李青林变得沉默寡言、孤傲不群,她对这个弱肉强食、丑恶黑暗的社会,感到无比的厌恶和憎恨。
1932年初中毕业后,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文史组学习。读书期间,她结识了中共党员任镜明、高宝书、邓本容等人,大家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34年师范毕业后,身材高挑、体魄强健的李青林到泸县第八初级小学任教,1937年转到泸县大北门小学任教。她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加入“全国抗敌后援会泸县分会”,组织发动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2月,经邓本容介绍,李青林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妇运工作,组织团结妇女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她动员部分女教师和女职员集资入股,开办“沱江女子商店”,为抗日救亡活动筹集经费。1940年7月,由于身份暴露,李青林化名李潭,转移到重庆“全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工作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进入慰劳总会,加强监视活动。7月,李青林返回泸县,到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小学担任教务主任,并兼任该校党支部书记,秘密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工作。1942年2月,由于受到兵工厂稽查组特务的怀疑,李青林化名李芳莲再赴重庆,在山洞中心小学任教。
由于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而辗转奔波,李青林一直没有解决个人问题。已经28岁的李青林开始和一个男青年初步交往,党组织调查发现,对方的身份和背景都难以确定,这在秘密斗争的环境中是十分危险的。在向李青林指出问题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与她的单线联系。李青林立即断绝了与那个男青年的交往,毅然离开原有的工作环境,应聘到磁器口市立第二十三中心校“夜课班”任教,并锲而不舍地联系、寻找党组织。
1943年,经党组织考察,认为李青林对党和革命是忠诚可靠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干部于江震派人恢复了与她的组织联系。根据组织安排,李青林先后到邻水县么滩小学、重庆南岸马家店分校、江北县莲华小学任教,负责组织开展妇女工作。1946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李青林调四川省委妇运组工作,参与创办《四川妇女》杂志。在与《新华日报》 联系的过程中,李青林与该报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青年才俊邵子南相识相恋,并相约结婚。年底,《四川妇女》被查封后,李青林被安排到基督教青年会识字班任教。
1947年2月28日清晨,李青林高兴地提着喜糖前往化龙桥,因为当晚她就要与邵子南举行婚礼,结为革命伴侣。不料,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在当天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曾家岩50号和化龙桥红岩村,强制扣留中共代表吴玉章以及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等有关工作人员。后经严正交涉,于10天后强迫所有被扣人员立即撤返延安。从此,李青林与邵子南这对将婚却又未婚的恋人便天各一方,再未相见。李青林先到牛角沱五姐(在华西公司工作)家里暂住,不久,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工作。
1947年7月,受党组织派遣,李青林赴万县工作。在去万县的江轮上,她决定以邵子南的一个笔名“青林”改作自己的名字。到万县后,李青林被安排在城郊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任教。她与该校校长贺辉(又名贺启惠,女,党员)、教师易明珍(女,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住在学校旁的贺家院子 (位于今万州区观音岩社区),一同开展革命工作。贺辉在2010年11月23日接受《重庆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8月的一天,学校来了一名30多岁的女教师,就是李青林。李青林高个子,齐肩短发,眼睛美丽而又炯炯有神,穿着花布衣,端庄质朴,举止沉稳干练。当时只知道她是上级派来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余的不能多问。
有一天,我提出想和李青林到照相馆去照个相作留念。没想到遭到李青林的严肃批评。李青林斩钉截铁地说,照相是在给敌人留把柄,党的纪律规定,这是坚决不能做的事。我这才恍然大悟,顿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幼稚。
1947年10月,中共万县县委正式成立,雷震任县委书记;李青林任县委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为了开展工作,李青林经常奔走于乡村、学校、秘密交通联络站等地,部署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组织党员学习,传达贯彻党的指示。她对党员们说:“目前的形势是好的,越是好的形势,我们的处境越困难。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员,任何时候都要保守党的秘密,做好牺牲的准备。”
对李青林在万县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贺辉回忆:
我们三人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常到明镜滩那些农户家去搞陶行知推行的小先生制,教农民识字,同时也了解一些情况。李青林这个事情抓得很紧,几乎一个星期有两三个晚上往农村跑。
每到周末,李青林都要到离学校约6公里的县城去。有一次,李青林叫我与她同去,我们手拉着手,走到一座桥头时,迎面走来一名女子。擦身而过之后,李青林小声地告诉我说,“她就是江竹筠!”我早就听说过江竹筠的名字,但我回过头去看时,只看到江竹筠的背影。
李青林十分重视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先后在进步学生中培养发展邓惠平、徐观蓉等学生入党。邓惠平于1983年4月在武汉所写《火炬接力棒——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万县学生运动的片段回忆》中写道:
李青林住在贺启惠同志家中,继续把贺启惠的表姐(车坝魏姐)家作为和我们联络的地方,她直接抓万女中(注:今万州第三中学)新民主学会小组的工作。她对我们布置的任务都由黄玉清同志转达……
遵照李青林同志的指示和学会小组的决定,我对外校同学广泛地进行了联系,在三条线上展开了活动。一条线是万男中(注:今万州第一中学,因那时只招男生,俗称万男中),主要接触的是汪燕生、刘培黎(即林特同志之子林培黎)、吴承汉等同学。另一条线是省职校(注:1944年创办的四川省立万县高级职业学校),主要接触的是丁耀庭、陆兴邦等同学,并通过丁耀庭和简师联系。再一条线是省万师,主要接触的是李蜀君等同学。我向他们推荐《大众哲学》,提供《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并和他们一起议论时政和各地学运情况……
所有这些活动,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概,使万县学生运动日益活跃壮大。
徐观蓉在回忆时,仍然清楚地记得她在1947年年底入党时李青林与自己谈话的情形:
大约九点钟,从外面进来一个女同志,高高的个子,圆脸,态度文静,和蔼可亲,穿件蓝色旗袍,衣着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好,这就是李青林同志。玉清向她介绍了我的名字后,我们坐下来,那天主要是青林同志讲话。记得开始时她把当时的形势简要地讲了一下,接着讲了党的纲领(并没有党章的本本,实际是凭记忆背下来的),领读了入党誓词。青林对我说,你的情况和表现都经组织考察过,我们研究决定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六个月。同时,她还讲了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纪律,并明确告诉我,从那天以后由她直接找我接头,不再和玉清有组织关系,要我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和她不是在约会时间、地点见了面不能打招呼,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盯梢等问题都讲得很仔细。她讲话的神态既平淡又严肃,讲完后坐了一会就先走了。
1948年4月,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传到万县,李青林预感到问题严重,便通知党员黄玉清、邓惠平、徐观蓉、贺辉等人,先后在贺家院子、一碗水 (原龙宝镇、今双河口街道)半坡上开会。要求大家:“万一我们这里出了事,任何情况都不要讲,要保守党的秘密,每个人都要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凡是与重庆方面有关系的,立刻中断一切信件往来,随时听从组织安排,要做好撤退准备。”
6月11日,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万县被捕叛变,致使雷震、唐慕陶、江竹筠、黄玉清、陈继贤等县委领导和一批党员先后被捕。14日下午,尚不知情的李青林像往常一样,径直往“表弟”雷震家走去。还在门外,她就喊道:“表弟!表弟在家吗?”“表弟媳”刘毓芳抱着年幼的儿子告诉她江竹筠、雷震出事了。刘毓芳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事情的经过:
6月15日(注:应是记忆误差,根据贺辉、徐观蓉、易明珍、邓惠平等人回忆为14日)下午,李青林到我家来了。
李青林(万县县委副书记)也是我家的常客,她的手工针线很好,每次见我给孩子缝衣服总爱帮忙,而且每次她离开时都是我送她到柑子园街外面。这天她也没进屋,就站在门口,我抱着孩子告诉她:“雷震出事了,你快走!”但是这天我昏了头,没想到问问她是否需要钱。我猜想她是因为没有钱了才回她教书的学校去的。要是我当时醒悟过来取下一只戒指给她,说不定她就逃掉了。当天下午她回到她教书的学校就被捕了,真令人痛心。这几天法院周围到处是特务,我是害怕特务发现后跟踪她,所以叫她快走。
其实,即使刘毓芳给了李青林路费,李青林也绝不会离开。县委书记雷震已经被捕,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李青林深感责任重大,她没有因为自身的安全马上撤离,首先想到的是赶紧通知组织其他党员迅速转移。在三马路,李青林遇见贺辉的邻居潘先生(做米生意),立即写了一张“赶快打扫清洁卫生,有客人要来”的纸条,委托他转交给贺辉,以便使贺辉能够及时销毁文件,安全撤离。
接着,她赶到电报路万丰糖果店,托人带信给徐观蓉:“近来,天气突然酷暑,玉清得了热病,你不要去看他,以免传染。城里瘟疫流行,最好到乡下住几天。青姐。”徐观蓉得信后于当日便转移到凉风乡下,躲过了大搜捕(新中国成立后任万县地区行署副专员、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离休后现仍居住在万州)。
然后,李青林匆忙赶赴几个秘密联络点和秘密通讯处,通知大家迅速转移。随即又赶到瓦厂街魏蜀军家,迅速处理完有关文件,准备前往不远处的德胜镇小学,通知在该校任教的黄玉清转移。恰遇邓惠平来到这个联络点,李青林便迅速安排她转移。邓惠平回忆:
我和汪燕生等从辅成法学院分部到城区辅成法学院本部参加演出。行到途中,遇到我的弟弟邓培生。他在豫章中学读书,是他的老师付寒松派来给我递信的,说是黄玉清于昨日被捕,要我注意。我当即对汪燕生同学说自己有点急事要办,请他先行一步。
汪燕生走后,我立即奔赴车坝魏姐家中。一进门,恰遇李青林同志在收拾文件。她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我们上边出了事,情况很紧急,你和玉清要迅速转移。”我告诉她,付寒松叫我弟弟通知我,说玉清昨日被捕了。李青林同志一听,便说:“你更要迅速转移。”我说:“在万县我恐怕呆不下去了,只有回故乡武汉去。”李青林同志果断地说:“也好。今后只要你继续为党好好工作,党会派人来和你联系的。”在她的催促下,我们便分手了。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李青林同志最后的一面。
我遄返家中,和母亲简要地讲了几句,带了随身衣服物品,只身前往沱口李蜀君同学家里。两三天后,丁耀庭、陆兴邦也来到李家,建议我转移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去暂避。他们回到省职,找何其芳同志的弟弟何海若老师商量后,决定送我到离万县六十多里地的河口场何海若家中去住几天。何海若的爱人沈明蓉,是我在万女中的同学,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住了半个月,何海若老师派人把我又送到沱口李蜀君家,再由我母亲找了条船,将我带回了武汉。从此,我便离开了我生活、学习和战斗过多年的第二故乡万县,参加了武汉的地下斗争,迎来了解放。
李青林送走了邓惠平,销毁了重要文件,于傍晚赶回贺家院子。进屋后,她对贺辉说:“地工委和县委主要负责人被捕了,黄玉清、陈继贤她们也被捕了。我们要准备路费赶紧转移。易明珍不是他们抓的对象,可暂时留下教书。”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6月15日上午,李青林继续在校上课,准备下午把预存的稻谷变卖成现金,作为路费和组织活动经费。中午,李青林与贺辉、易明珍一起商议变卖稻谷和转移的事。将近两点时分,只听见贺辉的伯父急促地喊:“启惠,有个先生找你。”李青林断然说:“特务来了!易明珍你出去说校长不在。贺辉快走。”贺辉迅速跑到远处一户农家,躲过了搜捕,随后转移去重庆,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贺辉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工作,后调入重庆钢铁公司任副经理、巡视员等职,1986年离休)。
李青林从侧门跑出,正要奔向山后密林,猛然想起学校还有一份文件,便转身向学校走去。刚走进学校,就碰上埋伏在那里的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率领的特务,李青林被捕了。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冉益智即向特务组长雷天元献媚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
当晚,在县城富贵巷4号党通局特委会刑讯室,雷天元主持对李青林的审讯:“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江志伟的人?”江志伟(炜)即江竹筠的化名,与李青林同在县委工作,与雷震住在万县地方法院同一栋楼。李青林坦然答道:“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整天都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无奈,特务只好使用酷刑这一招。他们把李青林绑上老虎凳,提起她绷直的小腿,将厚厚的砖块塞进她的脚跟下。顿时,李青林痛得满头大汗。
雷天元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谁是你的同伙?”李青林扬起汗湿的头,忍着剧痛,大声说道:“不是!我不知道!”雷天元大怒道:“我看你嘴硬。不说再加!”随即,特务粗野地在李青林的脚跟下又塞进一块厚厚的砖。李青林忍着钻心的剧痛,大颗大颗的汗珠像雨点般流下来,一言不发。
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吼道:“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直至右腿被折断,人已经昏迷不醒,她依然反复地呓语着“不知道”“不知道”……特务们一无所获,只好把昏迷不醒的李青林拖回牢房。
随后,特务将李青林等共产党人押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楼下的女牢室。由于李青林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因此也成为渣滓洞和白公馆受刑最重的“女犯”。她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同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狱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但除雷震、唐慕陶在男牢室外,女牢室的李青林、江竹筠、黄玉清、陈继贤,原汁原味就是原来的中共万县县委班子,她们组成女牢室与监狱特务顽强斗争的领导核心。在她们的组织领导下,女牢室先后关押的二十多名女革命者,都勇敢顽强地经受住严酷刑罚和非人生活的考验,个个意志坚定,人人宁死不屈,让后人们无不钦佩地得出“女人无叛徒”的结论。
由于长期遭受酷刑折磨,李青林在狱中常常因伤或因病卧床不起。只要能走动了,她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女牢室与刑讯室之间,积极组织参加狱中的各种革命活动。亲密战友江竹筠十分佩服和尊敬她,多次说:“我算不了什么,李青林受刑更重”(在小说《红岩》中,李青林的许多事迹都融入“江姐”的人物形象之中)。李青林平时沉静少言,但说出话来就很有分量,大家都尊敬地称她为“大姐”。她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分析问题深刻中肯,提出的办法可行可用。无论开展什么活动,大家都主动征求她的意见。当曾紫霞(后被营救出狱)因流言误传她的恋人刘国鋕变节(刘国鋕实际上是意志十分坚定的共产党人,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原型)而受到大家冷眼,情绪低落时,李青林便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并说服动员狱友们理解她、关心她、支持她,使曾紫霞重新振作起来,坚定与特务们继续斗争的勇气。在李青林、江竹筠的带领下,女牢室的狱友们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团结友爱,亲如姐妹。
在行动不便时,李青林常常坐在室中,为狱友们缝缝补补,照看伤者与婴儿。有时,她还拄着拐杖去为伤重的狱友洗衣服。一些男室的狱友入狱后没有冬衣,她就用旧衣服为他们缝制5件棉背心,还绣制了许多枕头,将组织的关爱与温暖传递到狱友之中。左绍英生下“监狱之花”,李青林便把五姐送来的罐头给她吃,以增加营养。李青林心灵手巧,尤其擅长绣花。她与张静芳绣出的枕套十分漂亮,看守们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为他们绣花、纳袜底等,并象征性地给一点微薄的报酬。由此,解决了狱中急需的洗漱、草纸等日用品。她曾为监狱看守长徐贵标的老婆绣了一对枕套。在可控的情况下,看守们还给女牢提供一些小小的方便,如狱内外代传物品、打听传递信息等。
李青林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她托人带话给五姐:“黑暗将要过去了,曙光快要来到。”并要求五姐给狱友们筹集路费。同时,她也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她曾带出纸条给表弟说:“这个医院很不好,脚的关节痛得厉害。将要转移到别的医院去。”
1949年11月14日9时许,监狱通知李青林、江竹筠“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李青林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她没有丝毫的畏惧,镇定自若地和女牢室的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她深情的向大家一一点头,连说:“同志们再见,再见!”然后果断地迈出牢门,江竹筠赶紧上前扶掖着她。
当她在江竹筠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出女牢室时,渣滓洞监狱响起了此伏彼起的“李姐”“江姐”的亲切呼喊声。两位亲密无间的战友手挽着手,微笑着向楼上楼下的狱友们频频挥手告别。在上囚车时,一个特务说:“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说:“别碰我,我自己走!”在江竹筠的帮助下,她艰难地爬上囚车,被秘密押往中美合作所礼堂看押。傍晚,李青林、江竹筠等30名革命者一起被押往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半个月后,重庆解放了。作为重庆接管干部的邵子南(后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副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四处打听寻找分别已久的恋人,不想得到的通知却是在电台岚垭掘出了李青林的遗体。邵子南悲痛欲绝,在烈士追悼大会上,他在李青林的遗像前撰写了一副挽联:
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
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首页
首页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数字方志库
数字方志库 方志园地
方志园地 重庆历史文化
重庆历史文化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