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府志》(道光年刻印)说“海棠溪在太平门大江对岸,源出南平山坞,沿壑带涧曲折入溪。溪边昔多海棠,骚人每觞咏其间”。《巴县志》(王尔鉴)里记载“在县南一里山川坛侧,多值花木,渝人以为游乐之地”。
清溪窈窕兰桡轻,荡入溪中烟水平。
两岸海棠睡梦醒,一村春酿香风生。
儿童树底逐金弹,少妇楼头吹玉笙。
清王尔鉴做巴县令时,从巴县衙门看长江南岸海棠绯红烟雨迷濛,慨叹不已,极为推崇名之“海棠烟雨”,称其为“巴渝十二景”之首,并写进他编纂的《巴县志》。他曾写下诗歌《海棠烟雨》赞美海棠溪美景,其诗曰:
溪邃怜香国,山容映海棠。
轻烟笼晓髻,细雨点新妆。
娟秀宁工媚,幽清却善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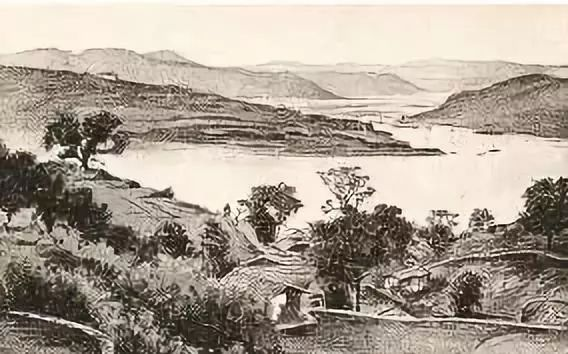
海棠溪渡口(作者选自网络)
更有坊间小说家言,说唐代女校书文采风流女诗人薛涛为了与元稹的真爱,曾追寻其脚步从成都到重庆海棠溪畔流连终日卿卿我我,还有《海棠溪》诗为证:
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
为充分表明薛涛游历过重庆,又拿出《谒巫山庙》一诗来证明。事实是《谒巫山庙》为薛涛呈递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投名状”,何况以薛涛当时的处境也不可能从西川跋涉千里之遥到三峡谒巫山庙。至于薛涛游历海棠溪一说,有重庆师范大学鲜于煌等多位学者考证并无其事,特别以二十八年来一直研究元稹的学者吴伟斌的成果有力,可参考他的专著《元稹考论》《元稹评传》。海棠溪并非重庆独有,成都称为海棠之乡,更早在唐宋时已是海棠遍种,花开之时,极尽艳丽之态,一片风流春色让人沉醉,连蜀中盛装美女也只能“花前顿觉无颜色”(陆游《海棠歌》)。薛涛终其一生也未到过重庆,那么她所写“海棠溪”,可能为她居住过的浣花溪或是西碧鸡坊。想来“薛涛笺”也是沉蕴了海棠的红艳而“洛阳纸贵”的吧。不过,这首关于海棠溪的诗歌确实描绘出了彼时重庆海棠溪盛景。所以《南岸志》说:“昔日,海棠溪水如带似练,潺潺不绝。每当春光明媚,两岸及岸边高埠海棠嫣嫣,修竹娟娟,径石儡儡,青草绵绵。若有晨雾轻拂,细雨霏霏,云烟袅袅,宛若霓裳飘逸,素帷落障;株株海棠恰似窈窕淑女遮纱掩绡,合睇微笑。”如此美景,南来北往行旅之人,无不驻足细赏;骚人墨客更是望溪息心,为之一醉。 随着社会的发展,海棠溪没于浩浩江水之中,两岸海棠树也销声匿迹,独留下“海棠烟雨”公园令人遐想。海棠溪又是古代川黔古道离渝的起点,其社会、经济意义不言而喻。王尔鉴编《巴县志》卷二《建置》“津渡”里记载“海棠溪——储奇门对岸,渡船十二,廉七甲,通廉八、九、十甲,孝七、八、九甲,忠三、四甲,节一、二、三、四甲米口” 。向楚编《巴县志》记载:“出储奇、太平两门,渡江抵海棠溪,川、黔往来要道也。城中居民数万,日需米薪杂物数百千,亦多由此道贩运而来,以故伫立唤渡者,踵止相接。” 《重庆市略志》载“惟由储奇太平两门到海棠溪码头,是川黔交通要道,每日返往频繁”。海棠溪渡口之重要可见一斑。因而王尔鉴慨叹“或横索于中流或贪多而重载” ,导致“行者慄股”,甚至有“贪边受赂”、“为害实大”。从记载可以看出,海棠溪渡口的船过江须收费。有待客人坐船到江中索要钱物,就如同宋江在贼船上被张横问“吃板刀面”还是“馄饨面”般,只能做待宰的羔羊。或者是船工贪于钱物而严重超载,多次发生渡船翻覆物失人亡的事故。有人多次向巴县衙门状,官府也三令五申,仍然是屡禁不止,直至一个人物出场,此种情形才稍有改变。这个人物叫杨霈,字慰农,汉军镶黄旗杨福山营佐领下人,道光壬午科举人,应该说曾三度出任巴县县令,后官至湖广总督,被太平军一顿狠揍后,朝廷以“坐视不救”罪撤杨霈之职,降职为荆州将军。《巴县志》(向楚)记载,县令杨霈为了改变海棠溪渡口的现状,拟设“义渡”,苦于衙门拿不出钱来,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专门设宴“大会绅耆,规设义渡”,意图募捐钱款。正在筹款艰难之时,时太和乡(今巴南区天星寺镇)廖春瀛、廖春溶兄弟俩遵先父廖尧勋(字国泰)遗嘱,捐出年收入田租357石谷子的田土,时值9288两银子。后又追加银子4712两,凑成1.4万两。这时,南岸下浩觉林寺 “寺僧不法,恣为淫荡”,将功德钱挥霍一空,把庙产200多石租子的田地,拿出去抵押了3000多两银子。

廖氏民居之骑龙穴
“义渡管委会”便用廖氏捐的银子,遣散僧人,盘下了觉林寺的庙田,全部计入义渡资产增加田产200余担,加上其他小额捐赠,海棠溪义渡最后每年可收田租760多石。时修造大船36艘,建造义渡管理官房6间,制定了规章制度刻石以记,并“申请川督题奏备案”。“当定案时提名为廖氏义渡,春瀛不欲以是得名,仍名为海棠溪义渡”。经3个月时间,于当年四月初二开船渡人。当日,渡口两岸“庶众欢而真武笑,山河秀而天地清,云飞川媚,巴歌渝舞,士女皆出,堤如人海”。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泽厚的儿子吴光裕又捐出田产折合830两白银纳入“义渡管委会”(《重庆府志》道光年刻印)。当时,海棠溪义渡由巴县东南两里的乡绅管理,廖家子孙也成了义渡的守护者。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经费不足,官府规定,以二十艘船渡人,不收船费,十六艘载货船酌量收取过河钱。再后来 “略取渡资,以便行客”,规定过江人每人收取船钱四文。后有人妄图借机敛财。廖姓后人眼看先辈义举受损害,因此向县、府、道反映,都察院回复:“海棠义渡,仍照旧章。”到了民国,市政府要接收义渡,廖氏子孙据理力争,“呈请省府,以义渡成立,系人民自由捐资,市府接收,于理未合。省府当喻以管理之责仍由县绅,监督之权移归市府,分明界划,可谓持平。讼争当有已时也”(《巴县志》向楚志)。事情就此了结。至今尚有望龙门洪学巷内“重庆廖氏捐助教养事业资产保管委员会”石碑及太和《廖氏族谱》记载为据。该义渡从创设以来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停办。时廖春瀛姻亲罗星(号春堂,綦江人,道光版《綦江县志》编纂者)写成七言古风一首并拟写条款勒石,记录了海棠溪义渡设立始末。
作者单位:重庆渝中区红岩村52号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大中小
大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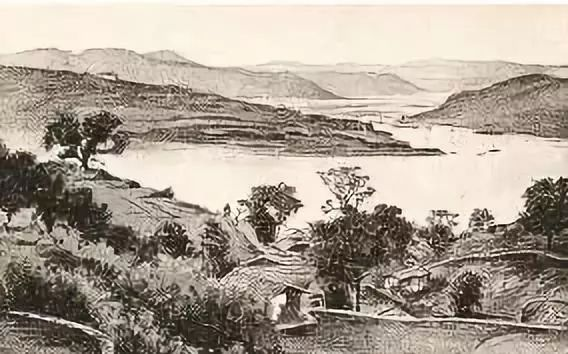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 数字方志库
数字方志库 方志园地
方志园地 重庆历史文化
重庆历史文化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


